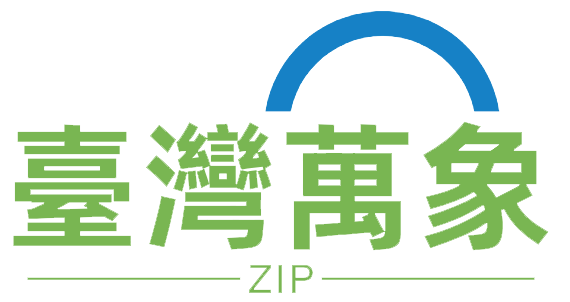矽谷的哈佛大學問題



(SeaPRwire) – 1976 年,納粹黨在美國的少數但堅韌的領導人弗蘭克·柯林計劃在伊利諾伊州的斯科基舉行一次遊行——這是一次旨在提升其組織知名度並為其事業尋求支持的嘗試。該鎮很多居民是猶太人,且曾經歷過戰爭,強烈反對這次遊行,並將此案告上法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基於第一修正案理由為柯林及其納粹黨徒辯護——這一舉動在今天幾乎無法想像。
當時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全國執行主任艾理·內爾收到了數千封信函,譴責其組織決定維護納粹份子的言論自由權利。內爾 1937 年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猶太家庭,並在兒童時期隨父母從德國逃往英國。他後來估計,由於該組織決定為納粹示威者辯護,導致 30,000 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成員離開了該組織。
他對保護柯林根據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權益的興趣並非源於對自由主義或其價值觀的盲目承諾。他反而持有兩種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又切實深刻而真摯的信念——既憎惡柯林的觀點,又認為維護柯林不受國家侵犯而表達其觀點的權利非常重要。他後來寫道:「為了捍衛自己,我必須用自由約束權力,即使臨時的受益者是自由的敵人。」他的信念是有代價的,而他的辯護讓他的組織和自己的信譽面臨風險。
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最近在國會作證——其中前兩位已辭去職務——引起了類似於近半個世紀前在斯科基出現的問題,包括在保護言論自由權利和防止企圖疏遠和征服他者的行為之間存在的熟悉的緊張關係。但該證詞還暴露了我們在美國和西方面臨的更重大、更根本的挑戰。
多年來,美國的廣大領導人,從學術管理人員和政客到矽谷的企業高管,常常因公開宣揚任何接近真實信念的東西而受到無情的懲罰。公眾領域——以及對那些膽敢做一些除了自我致富之外的事情的人進行的膚淺而卑微的攻擊——已經變得如此絕情,以至於共和國剩下的只有一些無能且通常空洞的人,如果他們內心深處潛藏著任何真正的信仰體系,人們會原諒他們的野心。矽谷的當前體系幾乎沒有給那些主要動機不是自我宣傳且往往不願讓自己屈服於現代公共領域的戲劇性和善變的、有能力且富有創意的思想家留有無餘地。
在近年來逐漸成熟的一整代管理人員和企業家中,本質上剝奪了他們形成對世界的實際觀點的機會——既描述性的(世界是什麼)又規範性的(世界應該是什麼)——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管理階層,其主要目的是往往似乎僅僅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和再創造。結果是,許多有權勢的人變得如此害怕冒犯任何人,以至於人們可能會根據他們的公開聲明推斷出,他們的內心生活和最私密的思想已經退縮到細小而膚淺的地步。變態且無心之過的結果是,銷售消費品的公司感覺有必要就影響到我們的道德或內心生活的問題發展並實際上廣播他們的觀點,而那些有能力且可能也有責任塑造我們的全球政治的軟體公司卻仍然顯著地保持沉默。
在 Palantir,我們為美國及其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國防和情報機構構建軟體和人工智能能力。我們的な仕事は物議を醸しており、誰もが米国軍のために攻撃用武器システムを可能にするソフトウェアを含む製品を構築するという我々の決定に同意す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私たちは、そのコストと複雑さに関係なく、選択を下しました。そして、多くの利益が見落とされています。フォーチューン上的我々の仕事の記事によると、後來成為美國國防部部長的詹姆斯·馬蒂斯的一名副手,曾經在國防部內部請求訪問我們的軟體時寫道:「由於此系統的功能,海軍陸戰隊員們今天才得以生存。」
大學校長們在國會作證時揭露了當代精英文化為保留權力而做出的交易——除了自己之外,對任何事物的信仰本身都是危險的,應當避免。矽谷體制對包括文化或民族認同在內的整個類別的思想變得如此多疑和恐懼,以至於任何接近世界觀的東西都被視為一種負擔。當被問及校園裡的反猶太主義時,大學校長們猶豫不決的證詞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其內容,而是因為其冷靜的精確性和精打細算——體現了新型行政類型的原型,即臨床謹慎,最重要的是沒有感覺。問題是,那些不說錯話的人往往根本什麼都不說。歌德在《浮士德》中提醒我們:「如果你沒有感覺,你就無法通過尋找來獲得它。如果你自己沒有湧現出來,你永遠都無法觸動別人的心。」
許多人認為這些校長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立場內在的矛盾——這些矛盾一方面源於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承諾,另一方面也源於他們的機構在其他各種情況下嚴格控制語言的使用。我們的文化在大多數情況下已成功地消除了那些領導著我們最重要的機構的人的任何狂熱和感情的音符或錯誤暗示。剩下的東西往往不清楚。當我們要求系統消除真正的人際接觸和與世界的對抗所必然伴隨的荊棘、倒刺和缺陷時,我們就會失去其他東西。加拿大出生的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對他所描述的「全機構」的研究可能在這裡具有指導意義。在 1961 年出版的一本名為《收容所》的論文集中,戈夫曼將此類機構(包括監獄和精神病院)定義為「大量處於類似狀況的個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與更廣泛的社會隔絕,共同過著封閉、正式管理的生活。」這一點同樣適用於我們國家的一些最精英大學,這些大學名義上且遲緩地向更廣泛的參與者敞開了大門,但其內部文化仍然相當封閉,與世隔絕。
在 1960 年代後期,包括耶魯大學的金曼·布魯斯特二世在內的前一代大學管理人員在面對和接受對根深蒂固的權力和精英特權的挑戰時採取了不同的路徑。1970 年 5 月,一系列涉及黑豹黨等人的民權示威席捲了耶魯大學校園,至少有兩枚炸彈在該校的冰球館中爆炸。然而,布魯斯特和其他人都願意以一種當今美國將迅速且概括地取消的方式來涉足當前時刻的道德泥潭。根據次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1970 年 4 月,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舉行的數百名耶魯大學教職員工會議上,布魯斯特表示,他「懷疑黑人革命者能否在美國任何地方獲得公正的審判。」他走進了這場大火,而不是遠離它。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
本文由第三方廠商內容提供者提供。SeaPRwire (https://www.seaprwire.com/)對此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
分類: 頭條新聞,日常新聞
SeaPRwire為公司和機構提供全球新聞稿發佈,覆蓋超過6,500個媒體庫、86,000名編輯和記者,以及350萬以上終端桌面和手機App。SeaPRwire支持英、日、德、韓、法、俄、印尼、馬來、越南、中文等多種語言新聞稿發佈。